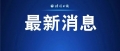桐城寻巷记
文/方国书
十一月初的安庆,清晨的风已带着明显的寒意。与爱人、朋友浮山游览之后,于七日傍晚时分入住桐城。
我和爱人虽籍贯贵池,但她的祖籍在桐城——这片我们从未踏足却始终心怀惦念的土地。初次踏上桐城,心中不免泛起层层波澜。
八日一早,桐城的天空是淡淡的青灰色,宛如浸透了墨的宣纸,含蓄而温润。太阳仍隐在云后,我们来到六尺巷景区。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石牌坊,右侧是一处小院,典型的徽派形制:灰砖、青瓦、白墙,素雅中透着文气。门楼上悬一副对联:“文章甲天下,冠盖满京华”,横批“文都桐城”。漫步于青石铺就的小巷,时间仿佛在此放慢了脚步,一股古朴宁静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六尺巷并不长,约百米,宽仅两米。两侧是高耸的灰墙,墙顶覆瓦,瓦下衬一段白壁,典雅中见节制。地面铺着细长的卵石,被岁月打磨得光亮照人。巷口立着一方文物保护碑,镌刻“六尺巷”三字。巷子不深,一眼便能望到头。墙头爬满藤萝,院墙内树木参差,枝叶伸展如盖,为巷子搭起一片清凉。
它静默地隐在寻常街巷中,若不特意寻访,极易擦肩而过。巷口石坊上,“礼让”二字已显斑驳。巷窄如其名,两人相遇,需微微侧身方能通过。脚下卵石光滑,石缝间探出细草,绿意渐褪,染着秋意。
我的目光流连于那一块块粗糙的墙砖——这大概就是当年张、吴两家的宅墙了。
清康熙年间,在京为官的张英接到家人书信,言及墙界之争。他回诗劝解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遂退三尺,吴家感其胸襟,亦退三尺,遂成此六尺巷。伸手轻抚微凉粗糙的砖面,仿佛触到一段宽厚的历史。这窄窄的巷子,度量的不仅是尺寸,更是人心的格局。
我们缓步走入巷中,踏着斑驳卵石,抚过灰砖墙面,恍如穿行于时光的隧道。巷内无人高声。一位白发长者扶着助行器,步履虽缓却稳,时而驻足,仰首望向被巷壁裁成细条的天空,又低头沉思。我听见他对身旁的老伴轻语:“争,是没有尽头的;让,才是海阔天空。”老伴眉眼慈祥,未发一言,只微微一笑,伸手为他理了理衣领。这一举动,胜过千言万语,道尽了巷中所蕴藏的精神。
巷仅百米,却藏有深意——空荡的巷道间,写满“胸襟”与“格局”。懂得礼让与包容的人,路会越走越宽。小至个人家庭,中至团体族群,大至邦国天下,莫不如此。
行至巷尾,见一小院。院中植有几株桂树,花期已过,枝叶墨绿沉沉。墙角苔藓茸茸,如铺了一层柔软的绿毯。在石凳上小坐,静听风过叶梢,看行人悄然往来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隔绝在这两墙之外。
回望长巷,人影渐疏。世上宽阔的路很多,但能让内心清澈安宁的,或许唯有这六尺窄巷。它静默不语,却将谦和与从容说得分明。那封从京城寄回的四句家书,比许多高墙厚垒更显分量。
我们在巷口合影留念,将这百米小巷与它所承载的千古之风一同定格。六尺巷已不仅是一处古迹,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——它所传扬的“礼让”,是一种修养,一种智慧,一种让世界变得辽阔的力量。
由此巷延伸开去,便触及桐城深厚的文脉。这片土地上,“五里三进士,隔河两状元”的佳话流传不息,“父子双宰相,兄弟四翰林”的传奇映照着世代书香。正是这醇厚的教化之风,孕育了以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文派,铸就了“天下文章,其出于桐城乎”的文学高峰。六尺巷的“礼让”与桐城派的“文章”,一者关乎德行,一者关乎文采,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温润而坚韧的文化脊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