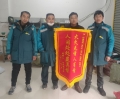□方珠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,老家在蚌埠二马路小巷子里。长长小巷的巷口东边出口是中山街,西边的出口是青年街。青年街和中山街都是二马路通向淮河坝子有名的街道。
我的老家就在长长小巷子的一个院子里。院子不大,有爷爷种下的一棵高大的香椿树。爷爷在树下埋了很多剩骨头汤、鸡肠子、鱼骨头等等做肥料,每到春天香椿树发芽,爷爷就守护着他的香椿树,不许人摘香椿芽,情愿给钱让家人去买。夜晚来临的时候,孩子们围坐在香椿树下听邻家大姐讲鬼怪神灵的故事。后来,夜幕降临,我一个人一直不敢走小巷子。

老蚌埠的街巷承载着深远的城市记忆。 王新民 摄
父亲在院里种下苹果树和梧桐树。每年春天,大人孩子都天天看着苹果树发芽,数着它开花,翘首期盼它结果。这是一棵苹果与梨嫁接的苹果树,每年只能可怜巴巴地结一两个果,全院七八个孩子都等着。父亲说,因为是苹果梨,所以特别金贵,能够吃上一口就是非常幸福和好运的事情了。那棵大梧桐树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,长得又高又大,父亲用旧砖头在树下垒砌围墙,供大家夏天洗澡。那是我记忆中最惬意的事情了。傍晚的时候,玩累了回家,吃过饭,躺在树下的大木盆里泡澡,树影婆娑,透过片片梧桐叶儿凝望着弯弯月亮和满天闪烁的星星,经常就把我带入了梦乡。墙外面排队洗澡的人喊:“怎么还没有洗好呀?赶快出来。”姐妹甚至还会进去,强行把我捞起来。
我们家祖孙三代同住这小院的老房子里。房子是木头结构,屋顶是灰色瓦片,一行一行排列着。房子一排四间,大门全是木头做的,门扇严实,有一些典型的中式图案设计,中间是一格一格的。冬天的时候,就买一些透明的纸糊上。夏天来临的时候,就捅破纸,通风凉快。厅堂的门有两扇,门很高大,一进厅堂,就是一张大桌子,是一个活动中心,一家人吃饭,议事、接待客人都在这里了。
爷爷是个裁缝,是二马路比较有名的裁缝之一,合作社的时候,带过不少徒弟。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徒。他总是说:过去学徒非常苦,什么事情都要做,就是要打杂很多年,师傅只教一点点,而且要求很严,动不动就被打,吃不饱,穿不暖。旧社会没有出路,总是期盼学好手艺可以过上好日子。最终,爷爷学得裁缝手艺,可以养家糊口了。爷爷做衣服打样,画线非常流畅,剪裁的布料非常平整,绝没有毛边,手工缝制尤其是缝制皮袄一针一线,密密麻麻,整整齐齐,绝好的工匠。我经常看爷爷做手工缝制,有的时候也想尝试,爷爷给我旧布头让我练习,而且是反复练习,从未达到过他的标准。爷爷完成了一件衣服,总是拎着领口,拽着袖口反复看,手艺人对自己作品追求精湛完美的那份执着,其中包含着一份自豪、自我陶醉和自我欣赏都写在脸上溢于言表。
父亲19岁参加抗美援朝,在汽车队负责运送物资。一次准备运送物资时,父亲的首长让他留下做内勤。他的一排的战友出发了,半路上汽车队遭到敌人的飞机袭击,全排的战友全部牺牲。每当父亲说起这件事情,坚强的父亲就会落泪。抗美援朝结束后,父亲的首长和战友们都留在了北京,父亲执意回到蚌埠,因为他认为自己为父母养老是一份责任,便回到了爷爷奶奶的住处蚌埠二马路的家。父亲为人谦和,乐于助人,单位分配房子,他总是让给更困难的人。父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,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家人,自己默默承担所有的生活压力。父亲长得很帅气,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他在汽车公司担任驾校校长时,正值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放映,学生和教练们都称他为大岛茂校长。父亲也负责处理交通事故,记得小的时候有人给家里送东西,父亲坚决不收,坚决退回。有一次有人送东西,扔下就走了,父亲让我拎着东西去追退回,我一直追到“天津水饺铺”,才追上那个人,退还了东西。父亲总是说,想起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,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公正的人,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,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

老蚌埠的小院子里有很多的故事。 夏炜 摄
我妈是一个漂亮的女人,结婚照片梳着长长的大辫子,经典的美丽。母亲的一张照片被当时蚌埠有名的照相馆——人民照相馆当作样片放大,在橱窗里展览,我们经常去看,并且向同学显摆。我妈非常能干,做饭洗衣,缝缝补补,啥都会做。过去洗衣服,都去淮河边清洗,冬天天气冷,要敲碎冰洗衣服。生活用水需要去固定的水站买水,然后挑回来用。日子虽苦,一大家人总是和和睦睦的。清晨早起,小院的问“早”声此起彼伏,迎接着新的一天开始。非常遗憾父亲60岁的时候脑溢血去世了。去世以后,我妈一直坚持自己单独住,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,每天和二马路上的老邻居一起去河坝锻炼。我妈永远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、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,86岁的时候,跟孩子们爬上了黄山,她说,来年再来。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周日家庭麻将聚会,母亲总是做好饭菜,等我们去吃,然后打6圈麻将。
我奶奶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的女性,但是她非常开明睿智。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总是在巷口等我放学回家,偶尔我发现她不在,我一定要去找她,找到她才算回了家。夏天的时候,邻居们都出来在马路上乘凉,我搬着小板凳,跟着奶奶一前一后走出巷口,在马路上乘凉,望着星星,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,我上班了,恋爱了,经常回家晚,我奶奶总是告诉我,无论什么时候回来,一定要告诉她。假如她睡着了,也一定要喊醒她,因为,她一觉醒来,不知道我是否回来了,会非常担心,一夜都睡不好。写到这里,我不能平静,鼻子酸酸流下热泪,好想念她。算起来,我奶奶已经去世32年,我总是在想念她,总是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,不让她担心。她让我感受到无条件爱的力量。她的爱让我享受终身,使我永远葆有着爱的能力。
我在高校工作,学校里老蚌埠人比较少,我也经常会和学生交谈有关蚌埠二马路的事,那些长长的小巷,小巷里住着人家,那里的一口井,那里的“sha”汤、油条、包子,还有雪园馄饨与元宵;二马路有一家卖板栗的商店,每天下午炒板栗,可以拿着一颗坏的板栗,到店里换个好的;1970年代,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放映时,人民电影院爆满,还曾拿着半张电影票混进电影院看电影;1980年代,二马路商业从地摊发展到全国闻名的批发市场,小商人们用布袋子装钱,回家后倒在大澡盆里数钱;也谈及从爷爷奶奶那里得知的日本鬼子占领蚌埠,以及我的长辈们在二马路生活的故事……一个人成年后的思维方式,行为模式与原生家庭有着密切联系,奠定生命的最基本理念。二马路长长巷子小小院暖暖的回忆,滋润着我的心田,给了我爱的动力,质朴纯真的灵性刻骨铭心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与血脉之中,代代相传。 (完)